目录
快速导航-
叙事 | 能饮一杯无
叙事 | 能饮一杯无
A 结婚第十六年,她已经习惯了老白侧身睡觉时略带腐腥味儿的呼吸和头发上飘过来的油脂气味。老白的睡眠一向比她强,几乎是一挨枕头就开始扯呼。起初她还感到些许困扰,不过经过多年的训练,也就成了习惯——她把老白的呼噜声和身上散发出的可疑气息都定义为一种婚姻内的适应性训练。她看着杯中物,暗红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摇曳,经吊顶上的水晶灯一照,竟有些玲珑之意。 老白爱侧身睡觉,还爱把脸对着她这边,年纪渐长之后又
-
叙事 | 鲸落
叙事 | 鲸落
我想是时候给你写一封信了。我第一次尝试给你写信是在十年前,你失踪后的第二个月。刚写下“妈妈”两个字,我的眼泪就疯狂地涌出。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办法给你写信,甚至再也没有办法回忆你。你一定为我故意忘记你而生气,所以这十年来,你才固执地不肯出现在我的梦里。真的很抱歉,我并非故意逃避你的存在,只是担心梦中相见时,你会为我糟糕的生活感到难过罢了。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轨迹是从出生那刻起就被上帝安排好的。读个
-
叙事 | 西亚的背影
叙事 | 西亚的背影
1 青年画家注意到西亚时,她正仔细调着颜料盘里的颜色,她很用心地将几种不同的色彩进行考究地拼配,她细致又轻巧,虽然不是很熟练,但很具有观赏性。青年画家坐在自己的画架前,眼前的一幅肖像画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但人物的刻画一直不是想要的效果,他的思路和灵感已经堵塞在这里,他隐约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他心里翻腾,奇怪的是他无法将这股情绪付诸笔端。他敏锐的双眼观察着西亚的侧身、后背,还有她抬笔描摹的动作,
-
叙事 | 五行
叙事 | 五行
木 夜深人静,一个声音从他身体深处悄然飘出,似有若无,时远时近:你的大限到了,你的大限到了……声音陌生又熟悉,像师父又不像师父,他明白,自己的阳寿要尽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要自己去”,今年正好是旬头年。研究命理多年,深知人生一世无非草木一秋,他对生死早已淡然,听到召唤,心里一点儿也不惊慌,静等大限来临。一生不长,几万个日子,经历太多太多,记忆太多太多,这么说来也够长。他抚摸着干瘪的身躯,心
-
叙事 | 迟到二十三年的葬礼
叙事 | 迟到二十三年的葬礼
一 二〇〇二年,我十八岁,大哥阿诺果果二十九岁,我们生活在乌蒙山里的石羊寨。大哥身材粗短,长着一张苦瓜脸,眼睛贼小,嘴巴特大,老实巴交,半天放不出一个响屁。好不容易说了一门亲事,女方虽腿带残疾,但脸盘子生得好看,本来是板上钉钉之事,没想到,我考取了省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所有责任落在了他肩上,他这一扛,个人的终身大事便耽误了。 父母去世后,给我们兄弟二人留下的唯一财产是屋后的一个小煤窑,为了凑
-
叙事 | 男人与树
叙事 | 男人与树
一九九一年,夏。具体地说是麦假的前一天,儿子将来结婚用的新房建成了。儿子十四岁,乡里上初二。新房位于村南的菜花地。三七墙,青砖,小椽,檩条,石灰的房面,五大间,占地一亩二。大秋后,全家从老宅子搬过来,该干什么干什么。男人和女人继续在村里当农民。种地,过日子,养活孩子,没事的时候串串门。三个子女继续上学,最大的高一,最小的初一。 第二年,夏。具体地说,是儿子中考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午,十点多。烈日当空
-
叙事 | 德彪
叙事 | 德彪
如果我说汤溪镇是个小镇,德彪一定不高兴,他会说:“汤溪镇怎么就小了?它有过五百年的县治历史呢。”如果我说汤溪镇是个大镇,他又会说:“汤溪镇可说不上大,你看人口和面积,跟麻雀似的。”德彪跟我同龄,我从未说服过他,跟他在一起,多数情况下我会对他的话采取默认态度。事实上默认也不行,他会认为这是沉默的反抗。真是不可思议,我这辈子怎么就和德彪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了这么久?有时候我想,如果小镇上没有德彪在,我会生
-
叙事 | 鱼跃冲顶
叙事 | 鱼跃冲顶
1 我看到一只足球冲天而起。我跟随这只怒气冲冲的足球一起冲出了“青鸟”足球基地。 我的左脚有点儿疼,我不知道是怎么弄伤的。也许是黄雄教练踹我的时候弄伤的,也许是万钧和江雨霆拦我的时候弄伤的,也许是我踢到了一个什么该死的东西上面弄伤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基地跑出来、怎样坐上出租车的。我只想离开基地,离开一切,找个没人的地方待一会儿。 整整一个下午,直到现在,我的脑袋里一遍一遍重复着基地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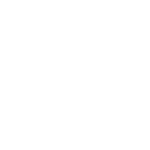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