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小说 | 寻找一棵柿子树
小说 | 寻找一棵柿子树
-
小说 | 井中小屋
小说 | 井中小屋
-
小说 | 半边人生
小说 | 半边人生
-
小说 | 盛暑
小说 | 盛暑
-
散文 | 单身母亲日记(二)
散文 | 单身母亲日记(二)
-
散文 | 卡瓦格博壮行记
散文 | 卡瓦格博壮行记
-
散文 | 荒野之上
散文 | 荒野之上
-
散文 | 老父亲
散文 | 老父亲
-
散文 | 南方的雪
散文 | 南方的雪
-
散文 | 铁匠、篾匠、泥水匠
散文 | 铁匠、篾匠、泥水匠
-
散文 | 俄色树下
散文 | 俄色树下
-
散文 | 我的故乡德格竹庆
散文 | 我的故乡德格竹庆
-
诗歌 | 转动川西(组诗)
诗歌 | 转动川西(组诗)
-
诗歌 | 手写体(组诗)
诗歌 | 手写体(组诗)
-
诗歌 | 天空之城(组诗)
诗歌 | 天空之城(组诗)
-
诗歌 | 秋的笛声(组诗)
诗歌 | 秋的笛声(组诗)
-
诗歌 | 过成云的生活(组诗)
诗歌 | 过成云的生活(组诗)
-
诗歌 | 雾天前奏(外二首)
诗歌 | 雾天前奏(外二首)
-
诗歌 | 姐姐(外一首)
诗歌 | 姐姐(外一首)
-
诗歌 | 最后的十月
诗歌 | 最后的十月
-
诗歌 | 忆
诗歌 | 忆
-
报告文学 | 路魂(节选)
报告文学 | 路魂(节选)
-
报告文学 | 2024年《贡嘎山》杂志年度作品暨授奖词
报告文学 | 2024年《贡嘎山》杂志年度作品暨授奖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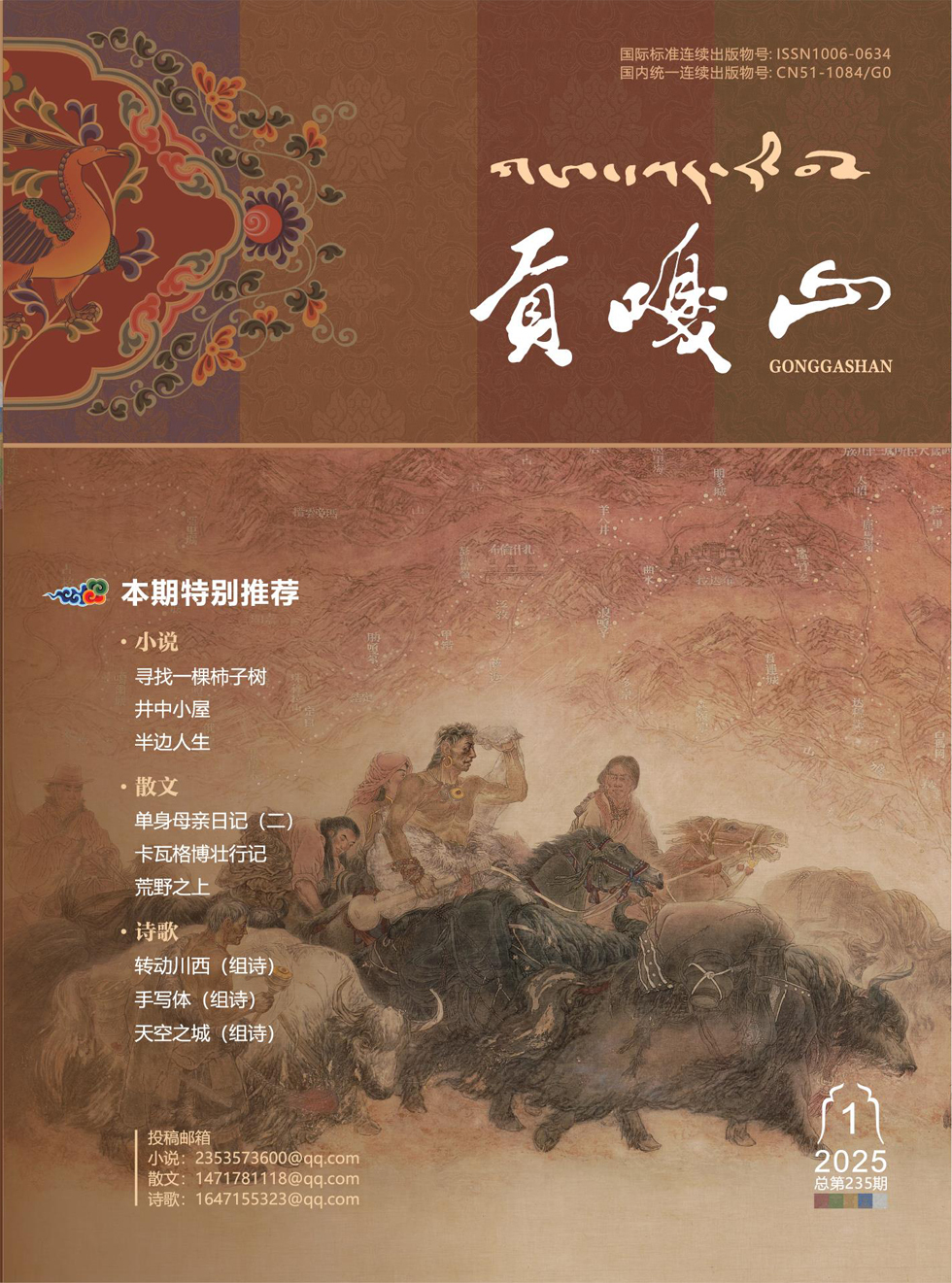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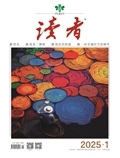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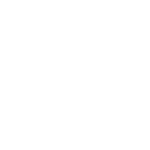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