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开篇作品 | 短篇小说两题
开篇作品 | 短篇小说两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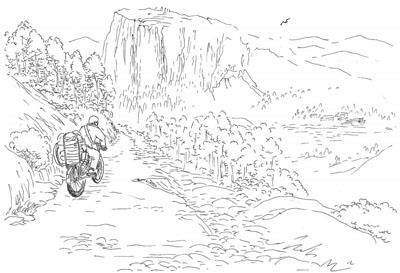
小说平台 | 过坎
小说平台 | 过坎
-

散文空间 | 我妈和她的宠物们
散文空间 | 我妈和她的宠物们
-
散文空间 | 有风吹过
散文空间 | 有风吹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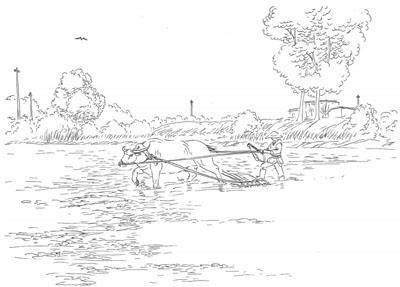
散文空间 | 父亲和田
散文空间 | 父亲和田
-
诗歌广场 | 也许不信(外五首)
诗歌广场 | 也许不信(外五首)
-

诗歌广场 | 马蹄河上(外六首)
诗歌广场 | 马蹄河上(外六首)
-

诗歌广场 | 走过博南山(组诗)
诗歌广场 | 走过博南山(组诗)
-

诗歌广场 | 在人间(组诗)
诗歌广场 | 在人间(组诗)
-
诗歌广场 | 远去的村庄(组诗)
诗歌广场 | 远去的村庄(组诗)
-

诗歌广场 | 苍洱诗萃
诗歌广场 | 苍洱诗萃
-

大理旅游 | 重走米甸红军路
大理旅游 | 重走米甸红军路
-

大理旅游 | 漫行苍洱间
大理旅游 | 漫行苍洱间
-

大理旅游 | 大理古城的柔软时光
大理旅游 | 大理古城的柔软时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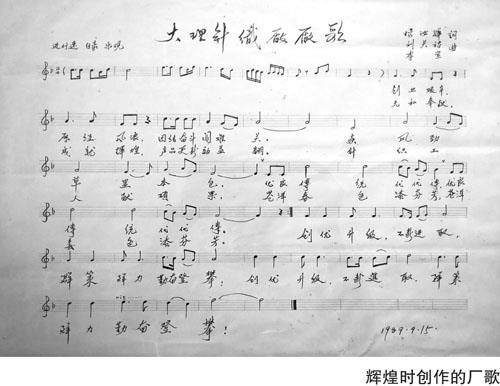
大理记忆 | 大理针织厂的回忆
大理记忆 | 大理针织厂的回忆
-
大理讲坛 | 家在白崖
大理讲坛 | 家在白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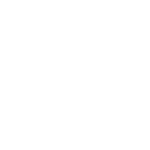
 登录
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