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快速导航-
首推诗人 | 在豚鹿岭上(十二首)
首推诗人 | 在豚鹿岭上(十二首)
入川断章 盆地内下着暴雪而四周的山上 全是阳光照亮的白色悬崖。我被 极端的气象所震慑,又被 迷狂与静止的 两种白色所吸引 而且,这不是我现在看到的场面 是少年时的记忆,猛然出现在脑海 由此我以为:当在暴雪中 失踪的少年又活着回来 ——被遗忘的极端美学,正好可以 替代现在思想上的分裂与平衡 松岗官寨远眺 雨中:碧山与河流是同一个走向 灰暗天空下一动不动地走 峡谷中头顶着
-
首推诗人 | 旅途上
首推诗人 | 旅途上
2024年夏天,在滇西南澜沧江两岸我走了两个月,之后,秋初时我还分别去过一次川西北和内蒙古。在旅途中写下了这组诗作。当然,它们不是“偶得”,甚至不是看见什么之后的“有感而发”——那段时间,我进入了一种偏执、热烈的写作状态中,想以寓言的方式呈现自然之物进入内心之后的真实景观。想把“我”认知的万物与肉眼所见的万物区分开来。诗作中的滇西南、川西北和内蒙古只是符号,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地名。 之所以有如此
-
首推诗人 | 记梦和旅行(十二首)
首推诗人 | 记梦和旅行(十二首)
梦中花 长梦中,经历黑暗、大火。 死过一次。 然后乌云,天将大雨。 洪水来临前,观察一朵花开。 身旁,断壁是坚固的。 湖心隐 湖对面是城市。 鸡、鸭、狗挤在一起看烟花。 我躺在石头缝里, 那边,烟花不是我放的。包括我主观意识。 在此之前,我们是观光团, 大屏幕滚动合影以做留念。 有横幅知道我是诗人,拉出一联对仗。 湿地上班 公司做公益,工牌埋进淤泥。 枯荷和鹭鸟刚学
-
首推诗人 | 关于记梦诗和旅行诗的创作谈
首推诗人 | 关于记梦诗和旅行诗的创作谈
记梦诗 太阳东升西落,我们的日常千篇一律,起床、上班、开会、吃饭、回家,即使是周末,也无外乎固定的几类活动。有时,写诗也是某种如常的活动,它们在驱使着诗人不断做自我复制:写,写下,不断写。而梦境却不一样,它危险又美丽,每次都有所不同。而且,据说做梦来自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大概占睡眠时间的20-25%,睡眠时间占一日1/3,也就是说做梦占生命长度的8.3%。时间如此长的精彩体验,我决定作一番
-
诗高原 | 定海珠(七首)
诗高原 | 定海珠(七首)
重访海口 ——致老友兼赠蔺永红先生 三角梅盛开的城市 南洋骑楼上革命的标语 如同活字印刷术一般古老 而早集上的蔬菜 以滚动的露珠 阐释太阳的新意 日日新,又日新 在摩肩接踵的百年老街 青春的向导今在何处 十八年前 你曾引我盘桓于此 又挥手告别 你是天涯的闯海者 和热情的主人 亦是时光的过客 在此烟火亲切的市井 空留酒旗 还有高高的槟榔树 伴随诗的残阳 在不
-
诗高原 | 地球旅馆(十一首)
诗高原 | 地球旅馆(十一首)
赠久无消息的朋友 好久没看见你的消息, 微博停更,朋友圈没有动静。 想必我们一样, 像两台报废的车辆, 将彼此遗忘于各自的荒野。 野草漫过车顶, 把一朵野花赠给远方吹来的信风, 我们的信息, 都弥散在风里。 一只候鸟落到方向盘上休息, 没多久又匆匆飞走, 它衔来的那粒种子开始发芽。 一株藤蔓长出来, 野草越来越茂盛,而你我 已经爱上这偏安一隅的际遇, 爱上这心安理得
-
诗高原 | 夜游偶得(十一首)
诗高原 | 夜游偶得(十一首)
夜游偶得 宇宙之黑暗止步于路边草丛 光的圆锥体,飞蚊症幻觉 越狱之蝌蚪文 翩然起舞 世道难平。虫子们喝水 或者作爱,为何发出 如此巨大声响,抑或 是对长夜的恐惧 一杆路灯投下的 光之帐篷、洒金小教堂 寂静的唱片,边缘融化 将坠末坠之汗滴 无有之人——每一次的合掌 俱在领受一颗 天外流星 伤 春 光合作用令这个时节的 色差及形状模糊:路边长椅上 端坐着平民化的消
-
诗高原 | 观窑记(六首)
诗高原 | 观窑记(六首)
参观邱吉尔庄园 其实,我们并没有进去 只是在外围转了一圈 这一圈就来到了泰晤士河边 那时他抽雪茄,戴帽子 那时他的手枪很时髦 如今铁门紧锁 庄重的房屋耸立着肩膀 是时候该担起这责任了 草坪青绿,树木茂盛 而鲜花从墙里伸出双手 这一切就像是启示 我们没有见到的东西 正在孕育风景 泰姆河 空气清新得像一把藤椅 躺在我的面前 鸟在身上按摩 水在血液里流淌 温暖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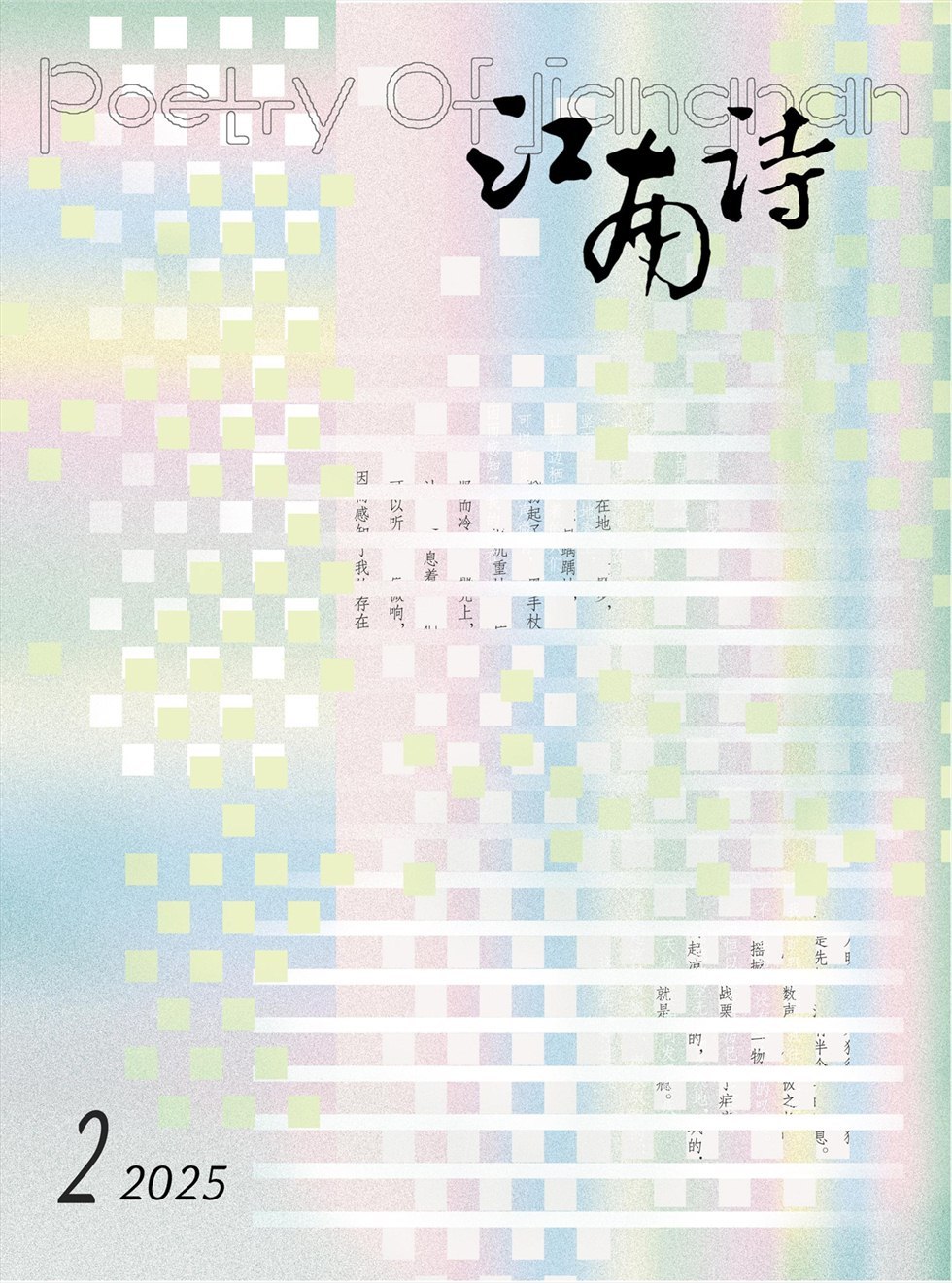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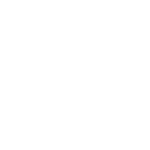
 登录
登录